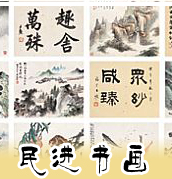莫言莫不言
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,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,使之成为该奖项设立111年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。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为:(莫言)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。同日,中国作家协会发表贺辞称:(莫言)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,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,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,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,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、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。两相对照,角度显有不同。
但我更关心的是莫言自己的表述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莫言谈到了他走上文学道路并取得成就的几许要点。
一是读书。莫言本名管谟业,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,少时村穷家贫,无书可读的现实反而刺激了他读书的愿望。莫言说:“那时候书非常少,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,为了看书,想尽了一切办法,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,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,帮人家推磨、割麦子,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。”这样的经历不能不令人想起袁枚的那句名言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联想到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对幼时读书的描写:“余幼即嗜学。家贫,无以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”这是一种怎样的痴迷和勤奋。莫言也曾如是说:“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,当时农村没有电,只有一盏小煤油灯。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像一个黄豆一样小,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,我们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。几年之后,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。”试想,如果当初的莫言坐拥书城,环境优越,还会有今天的诺奖获得者吗? “《七略 》《四库》,天子之书,然天子读书者有几?汗牛塞屋,富贵家之书,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?”(《黄生借书说》)书多了反而不读,这真是一个悖论。但这并不能说明书多了是坏事。读与不读,不在书的多少,而在于读书的环境与氛围,还有教育的取向。于今的孩子大不缺书,然真读书者有几何?检讨我们的学校、课堂,除了做题考试,又给了孩子多少自由读书的机会和热衷读书的动力?
二是亲近自然与生活。莫言说:“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。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,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。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。有时候躺在草地上,看到天上的白云,听到鸟叫,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,和大地发出的气味。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,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,都让我想入非非。”与自然的亲近所获得的其实就是自由。想当初,童年的鲁迅和弟弟躺在床上,仰望着星空,漫无边际地编着故事,显然这样的生活成就了他们后来的创作。可现在的孩子呢?上学被圈在教室里,放学被送进补习班,生活被别人摆布着,不接地气、不得自由,哪来的灵气与创造?难怪有作家愤怒地质问学校教育:“我的那个写出‘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痒’的孩子哪去了?!”莫言说:“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,故事、人物,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有的是邻居的、亲戚朋友的经历,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,这是一批最原始、最宝贵的素材。”“莫言在中国农村长大,到17岁还干着照管牲畜、收割高粱等农活,借着油灯光听老一辈讲述那些充满鬼神的中国民间故事和传说,是他小时候唯一的娱乐,童年的艰苦生活是他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。”《费加罗报》如此评论。
三是动机。莫言曾说自己的写作是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的。”他讲,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,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“腐败”的作家——一天三顿吃饺子。“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。我就问他:‘叔叔,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,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。’所以,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,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。”这显然不是一个高远的目标无法与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相比肩,但这并没有妨碍莫言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、一位有担当的作家。莫言说:“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应该暴露黑暗,揭示社会的黑暗,揭示社会的不公正,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,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。”但这是他此后的认识,生活的赐予。我们没有理由据此怀疑当初那个想“吃饺子”的动机,诚如当年许多人因为吃粮、逃婚、赌气而投奔革命,但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成为英雄或革命家。
莫言是诚实的。这样的诚实告诉我们,动机有时并无高下庄谐之分,只要你喜欢,你向往,你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并有所收获。特别是小孩子一开始写文章,兴趣是最主要的。我在一篇题为《有趣就好》的文章里曾写过:女儿读一年级时,时常从学校带回些小朋友自编的歌谣,说不上有多大的意义,但是听起来很有趣。有一首歌谣是这样的:“你看你大哥,挣钱多么多,买了个箱子,搬到墨西哥;你看你大嫂,挣钱多么少,捡了块手表,一年走一秒;你看你老爸,黑社会老大,买了个大哥大,不会拨号码。”——的确没多大“意义”,但就是有趣,不仅孩子喜欢,连大人没事念两遍,也觉得开心。这样的“写作”因为不预先追求“意义”,而使文字有了自由的空间和可贵的情趣。这就是真话,是小孩子最真实的“写作”动机。
莫言说,他的笔名“莫言”就和喜欢讲真话有关,“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。”什么时候,我们的教育也能教孩子们莫不讲讲真话,而再莫言假话、空话、废话、官话。如莫言老师所说:“该怎么写,还怎么写;想怎么写,就怎么写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可以是孙子,是懦夫,是可怜虫,但在写小说时,我是贼胆包天、色胆包天、狗胆包天。”有这等气魄,再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未可知。